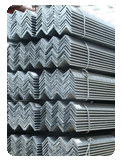它就在我桌角的左前方,静静地立在一个素白的瓷盆里。说是盆栽,倒更像一座微缩的、沉郁的森林。这株胡椒木的枝叶生得极茂盛,拥挤着,交叠着,撑开一团近乎球形的、浓得化不开的墨绿。它不像那些开着娇艳花朵的植物,需要人时刻去关注它的悲喜;它只是沉默地待着,仿佛我忙碌或闲暇,都与它无干,它自有其完整而独立的世界。
凑近了看,才发觉这片墨绿并非单调。那些卵形的叶片极小,却极密,一簇一簇,围着纤细的枝条轮生开来,像一把把撑开的、绿色的小伞。叶片表面是油亮的蜡质,日光灯清冷的光线落在上面,并不渗入,只浅浅地浮着,漾开一圈柔和的光晕。而叶背的颜色则浅了许多,是一种哑光的灰绿,隐隐能看到纤细的脉络,如同隐秘的地图。我有时用手指极轻地拨弄一下,它们便微微颤动起来,发出细碎到几乎听不见的沙沙声,像是梦呓。
最有趣的,是去端详它的枝干。主干其实只比筷子粗些,却嶙峋盘曲,裹着一层深褐色的、粗糙的树皮,裂着细密的纹,竟有几分古树的苍劲之气。从这主干上生发出的枝条,又是另一番模样,是秀气的棕红色,光滑而富有生气。这一老一嫩,一枯一荣,奇妙地结合在一处,便凝聚成一种沉稳的力与美。
看得久了,我常觉得它不像我案头的摆设,反倒是我,像个闯入它寂静疆域的不速之客。我的周遭,是键盘的敲击声,是文件的翻动声,是电话的铃响,是奔流不息的时间。而它的世界,节奏却缓慢得近乎凝滞。生长是以毫米计算的,呼吸是在悄无声息中完成的。我们共享着同一片空气,却仿佛处在不同的时空维度。
给它浇水,是我与它最郑重的交流。清水缓缓渗下,浸润那深色的土壤。我仿佛能听见它根部贪婪的、欢愉的叹息。水珠偶尔溅在叶片上,便凝成晶莹的珠子,在叶心滚来滚去,最后倏地一下,不见了踪影。这时的它,绿得愈发鲜活、湿润,像一场雨后的山林。
于是,当我从繁密的工作与文字中拾起头,目光与这片沉静的墨绿相遇时,心上的尘埃便仿佛被悄然拂去一些。它不言不语,却给了我一份安然的陪伴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