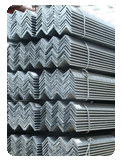时间这东西,向来是不由人分说的。它自顾自地流,把黑发漂成白发,把挺直的脊梁压成弯弓。然而在我母亲身上,光阴的痕迹却非仅是摧折,更是一种深沉的酿造。
幼时记忆里的母亲,是灶台前一团忙碌而焦灼的影子。彼时家贫,她的光阴被切割成无数碎片,填进灶膛成为火,混入猪食成为糠,缝进全家老小的衣衫成为密密的针脚。我常见她一边烧火,一边纳鞋底,额上汗珠滚落,尚不及擦拭,便叫我们兄弟之一的声音唤了去。她的时间如此廉价,廉价到可以被任何家事、任何旁人随意支取、割裂。她像一只永远转不停的陀螺,被生活的鞭子狠狠抽打着,在方寸之地留下磨损的印痕。那时我以为,母亲是没有属于自己的光阴的,她的日与夜,皆是我们的。
年岁稍长,外出求学,母亲的光阴便缩成了一封封家信。她的字大而端正,每一笔都用力透纸背,仿佛要把叮嘱刻进纸的纤维里。信里无非是“家中一切安好”,“钱够不够用”,“专心读书”之类的平淡话。然而后来才从父亲口中得知,每写一封信,她都要戴上老花镜,在灯下斟酌良久,写错了字,必要撕掉重来,绝不敷衍。那灯下写信的时刻,大约是她忙碌岁月里,唯一能偷出来、专门用于思念的,属于她自己的光阴。那光阴被折叠进信封,贴上邮票,便开始了跨越山河的跋涉,直至落入我手,展开时,仍带着她指尖的温度和一种郑重的墨香。
后来,我立业成家,母亲也老了。她终于从无尽的操劳中解脱,光阴似乎一下子宽阔起来,却也被陡然抽走了内容,显得空荡而迟缓。她坐在阳台的老藤椅里,一坐就是半天。阳光一寸寸挪移,从她的脚尖爬到膝盖,再漫过膝头的旧毛毯,最后从银白的发梢悄悄溜走。我起初以为她是寂寞,买了电视,劝她下楼走走,寻些老友聊天。她总是答应着,却仍最常坐在那里。直到某个午后,我见她并非呆坐,而是眯着眼,看楼下嬉闹的孩童,目光随着那小小的身影移动,嘴角含着极淡的笑意。我忽然明白,她哪里是在消磨光阴,她分明是在温习。那光阴虚虚实实,映照的或许是几十年前,同样在院子里奔跑啼哭的我。她的光阴不再向前奔涌,而是成了一潭深邃的湖水,过往的种种沉淀在水底,被她一遍遍打捞、回味。此刻的她,终于成了自己时间的主人,尽管这时间已满是夕阳的余温。
前几日为她梳头,握着一把稀疏苍白的发,心如刀绞。她却拍拍我的手背,笑道:“人都有老的时候,头发白了,倒是省了电灯。”她竟拿自己打趣起来。我这才惊觉,光阴赋予她的,不只是皱纹与衰弱,更有一种通透与和解。她不再与生活较劲,而是安然地坐在光阴深处,像一座被岁月河水冲刷得圆润的礁石,沉静地接受所有的潮来潮往。
母亲的一生,何尝不是一片被岁月耕耘的土地?光阴是犁,最初在她身上划开一道道尖锐的沟壑,埋下辛劳与付出;最终,却又用同样的力量,抚平那些创口,让智慧与从容从伤口处长出,开花结果。她交付出去的是青春与力气,光阴偿还给她的,是一种深水静流般的沉静力量。
我如今也到了不惑之年,常常感到时间被事务撕扯得七零八落。每于此,便想起阳台上的她。于是定下心来,知道不必慌张。因我身上流淌着她的血,亦将传承她与光阴相处的方式——在付出中坚韧,在等待中沉淀,最终在生命的黄昏,与所有过往达成谅解,安坐在一片金色的宁静里。(汉钢公司 樊红军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