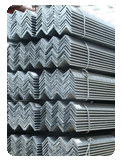小的时候,最羡慕同伴的家里有一辆摩托车,每次看见邻家父亲骑着摩托车风驰电掣而至,轰隆声如春雷滚过,留下一道青烟,也把一道羡慕的烙印深深刻在我心上。那时,摩托车实属稀罕物件,唯有家境殷实者才可拥有。我眼巴巴望着小伙伴绝尘而去,只能把羡慕和那未散的青烟一同吸进肺腑,又默默咽下。
初二那年,父亲终于也添置了一辆摩托车。那天晚上,家中摆了两桌酒席,父亲的好友们高声祝贺他喜提爱车。门外鞭炮噼里啪啦炸响,漫天纸屑如蝶纷飞,我悄悄走近那崭新的蓝色豪爵摩托,伸手抚摸冰凉的车身,低低祝福道:“爸爸出入平安。”那声音被鞭炮声吞没了,却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沉甸甸的种子。
自此,父亲便与这个伙伴形影不离。他骑着它奔赴一个又一个工地,无论晴雨寒暑。那摩托车上,总斜斜绑着他那起了毛边的工具包,装着那把油亮厚实的砖刀,刀柄处磨出深深凹陷,如同父亲手掌上厚厚的老茧一般,都是光阴咬下的印记。它载着父亲在风里雨里奔波,也载回了全家人的生计和希望。
每遇逢年过节,走亲访友,我便最爱攀上父亲摩托车的后座。车一发动,风便迎面扑来,路边的树影与田野急速向后退去,我贴着父亲宽阔的后背,仿佛贴住了一座安稳的山峦。车子疾驰,风声在耳边呼啸,我心中竟也似生出翅膀,自由地飞起来,却又被父亲后背的温暖稳稳托住——风越急,父亲后背的温暖反而越清晰。
后来,我升入高中,父亲谋生的足迹也渐渐伸向更远的异乡。摩托车后座上的日子,便如沙漏中的沙,无可挽回地滑落、减少、终于消失。我负笈远行,奔赴他乡的学堂,父亲则暂别那匹日渐老迈的铁马,奔向谋生的远方。
再后来,我便如蒲公英的种子般飘落异乡,开始独自谋生。时间像无情的潮水,冲刷掉许多东西,也冲淡了归家的次数。
这一次离家时,我特意选了最晚一班火车,父亲执意要用摩托车送我去车站。于是,相隔多年,我又一次跨上了那熟悉的后座。
父亲今日骑得极缓、极小心。昏黄路灯的光晕流淌在他身上,我凝视着他微驼的背影——那曾经宽厚如山的脊梁,仿佛已被岁月削薄。头顶逐渐稀疏的头发和脖颈间深深的沟壑仿佛诉说着他已不再年轻。父亲沉默地握着车把,载我前行。那些呼啸在风里的年少时光,仿佛已被缓慢的车速远远甩开,在身后模糊成一片迷离的烟尘。
摩托车终于停在火车站前。我缓缓下车,父亲摘下头盔,那张被岁月反复雕琢的脸孔在灯光下完全显现,沟壑纵横。他什么也没说,只是对我点点头,挥手示意我快些进站。我转身进站,再回望时,父亲依旧跨在那旧车上,身影在空旷的站前广场上,竟渺小如一粒微尘,又固执地凝固成一座沉默的山丘。他停驻原地,执着地目送我的背影,如同当年我在街角目送他摩托车的尾灯消失于黑暗深处那般——人生两端的凝望,中间竟横亘了如此汹涌无情的岁月之河!
车站的电动扶梯无声地载我上升,父亲的身影终于被缓缓淹没。在机械的上升中,耳畔似乎又响起了那辆旧摩托引擎的轰鸣——那声音从记忆深处传来,曾经载着父亲奔向生活的战场,也曾载着我奔向未知的远方。它负载过我们两代人的道路与重量,却终究载不动那疾驰如箭的时光,更载不回父亲在鞭炮碎屑中熠熠生辉的青春容颜。
时光的摩托车,终究是单程的奔赴;父亲的后座,成了我再也回不去的原乡。我多想坐上那后座,回到那年鞭炮炸响的夜晚,对着崭新的车身,再说一遍那被淹没的祈愿:父亲,我多愿您再年轻一回!(汉钢公司 胥京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