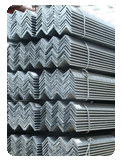老屋门前的那棵樱花树又开花了。粉色的碎花藏在墨绿的叶间,风一过,就簌簌地往下落。我站在树下,看着母亲踮起脚摘樱花的身影,忽然觉得这场景熟悉得让人鼻酸——十年前,她也是这样摘樱花给我做零食的,只是那时她的腰板挺得笔直,不需要扶着树干歇气。
父亲在院子里修那把老藤椅。阳光透过葡萄架斑驳地洒在他花白的头顶,他眯着眼睛,用粗粝的手指捻着藤条,动作慢了许多。这把椅子比我年纪还大,自我记事起,父亲就在修它。年轻时他三下五除二就能补好的破洞,现在要花上一整个下午。藤条在他手里翻飞,发出细微的"咯吱"声,和着树上偶尔的鸟鸣,竟谱成了最安心的生活乐章。
厨房里飘出红烧肉的香气。母亲固执地不用高压锅,就爱用那口老砂锅小火慢炖。她说这样的肉才入味,就像日子要慢慢过才有滋味。我进去帮忙,看见灶台上摆着三个碗——大中小,从小到大都是这样的排列。母亲舀汤时总会先尝一口中间那个碗的咸淡,因为那是我惯用的碗。这个动作她做了三十多年,成了改不掉的习惯。
晚饭时父亲照例要喝两盅。酒还是那种廉价的粮食酒,装在掉了漆的锡壶里。他给我也倒了一小杯,就像我十八岁那年他第一次允许我喝酒时那样。我们碰杯的声音惊醒了趴在桌下的老黄狗,它抬头望望,又安心地睡去。母亲在一旁絮叨着少喝点,却不忘把最瘦的肉夹到父亲碗里。这样的对话,我听了半辈子
饭后我抢着洗碗。母亲站在旁边擦灶台,忽然说:"你小时候最不爱洗碗,每次都要你爸用一块钱贿赂。"水龙头哗哗地响,我低头看着洗碗槽里泛起的泡沫,想起当年为了攒钱买连环画,确实没少跟父亲讨价还价。现在那套《三国演义》还放在我旧房间的书架上,父亲定期会取下来掸灰。
夜渐深了。父母坚持要我睡以前的房间。床单是母亲新换的,带着阳光的味道。我躺在床上,看见天花板上还留着小时候贴的荧光星星,只是现在它们不再发光了。隔壁传来父母压低声音的谈话,内容无非是明天要去早市买什么菜,后院的菜地该施肥了。这些琐碎的对话,却让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安宁。
清晨被豆浆机的轰鸣吵醒。父亲在院子里打太极拳,动作比年轻时慢了一半。母亲在厨房煎油条,围裙上沾着面粉。见我起来,她立刻把第一根炸得金黄的油条夹到我碗里:"快吃,凉了就不脆了。"这样的早晨,在我离家工作的十年里,曾无数次出现在梦中。
要返程时,母亲往我行李箱塞满腌好的咸菜、自制的辣酱,还有一包晒干的桂花。父亲默默把我的车检查了一遍,加满了玻璃水。后视镜里,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,最后变成两个模糊的黑点,却在我心里无限放大。
回城后某个加班的深夜,我打开母亲给的辣酱拌面。辛辣的味道窜进鼻腔的瞬间,忽然就湿了眼眶。原来幸福从来不需要惊天动地,它就藏在父母等你回家时亮着的那盏灯里,在他们记得你所有喜好时的那种固执里,在他们日渐迟缓却从未停止的爱里。
樱花香里修藤椅的老人,灶台前絮絮叨叨的妇人,构成了人世间最温暖的风景。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这寻常巷陌里的相守,这烟火人间中的相伴,才是命运给予我们最奢侈的馈赠。(汉钢公司 文惠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