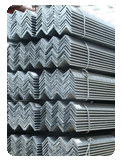那肩膀并不宽阔,甚至有些瘦削,却是我童年记忆里最安稳的港湾。
记得幼时生病,父亲总爱背我去诊所。夏夜里,他的肩胛骨硌着我的胸口,我能闻到他衬衫上淡淡的汗味混合着烟草的气息。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,我趴在他背上数着他的脚步声,一、二、一、二,竟比数绵羊更能催人入睡。他的肩膀随着步伐轻微起伏,像一艘小船,载着我渡过发烧的混沌。
父亲是个木匠,他的肩膀常年扛着木料。我常常蹲在作坊门口,看他扛着沉重的木板走来走去。那些木板压在他肩上,留下浅浅的红痕,他却从不叫苦。阳光透过木屑飞舞的空气,落在他的肩膀上,汗水在那里汇成细小的溪流,顺着脊背蜿蜒而下。有时他会让我骑在他脖子上,带我去看刚完工的家具。从那个高度望下去,世界突然变得不一样了,我能看见作坊顶棚上筑巢的燕子,能望见远处山坡上的野花。
十二岁那年,我在学校打架,被请了家长。回家的路上,父亲走在前头,我垂头跟在后面。突然他停下脚步,蹲下身说:“上来。”我迟疑地趴上他的背,才发现自己已经很久没有这样亲近过他了。他的肩膀比记忆中单薄了许多,我能摸到突出的肩骨。他把我的书包也拎在手里,什么都没问。晚风送来他身上的松木香,我的眼泪悄悄落在他洗得发白的衣领上。
上大学离家那天,父亲执意要帮我扛最重的行李箱。在车站,他把箱子举上行李架时,我分明看见他的手在微微发抖。火车启动时,他站在月台上挥手,肩膀在宽大的外套里显得格外瘦小。我突然想起小时候他背我去看病的夜晚,那时的肩膀,明明能扛起我的整个世界。
去年回家,发现父亲的右肩比左肩低了些许。母亲说,是常年扛木料落下的毛病。夜里给他揉肩时,触到皮肤下凹凸不平的骨头,还有几处陈年的伤疤。他笑着说没事,却在我力道稍重时忍不住吸气。这个曾经能轻松背起我的肩膀,如今连一件厚外套都觉得沉重。
前些天整理旧物,翻出一张老照片。照片里的父亲正扛着木料,对着镜头憨厚地笑。阳光照在他的肩膀上,镀了一层金边。我忽然明白,父亲的肩膀从来不是最有力的,却始终稳稳地托起了我们的生活。那些被木料压弯的弧度,正是他爱我们的形状。
现在每当我抱起自己的孩子,让他坐在我的肩头看远方时,总能感觉到一种熟悉的重量。那是从父亲肩膀上传承下来的,关于爱与责任的重量。我的肩膀或许比父亲的宽阔些,但我知道,永远也不及他的肩膀承载得多。
父亲的肩膀,是我人生的第一座桥,渡我长大;如今它成了一道斑驳的栏杆,需要我小心搀扶。岁月是最无情的木匠,将曾经挺拔的木材雕刻得日渐佝偻。但在我心里,那个在路灯下背着我稳步前行的背影,永远年轻,永远有力。(汉钢公司 郭超锋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