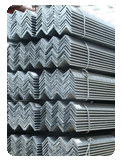柞水的四季是把算盘,打得清爽分明。春是山桃野杏漫出来的粉,夏是秦岭深处浸在溪水里的绿,冬是雪落秦岭时压着松枝的白,到了秋,便成了一场雨一封信,拆开时总带着点凉津津的新意。
最先察觉秋来的,该是山尖的风。先前夏末的风还带着溪涧的潮气,黏在皮肤上是温吞的,忽然某夜落了场雨,不是夏日常见的瓢泼,是细密的,像谁把云撕成了絮,飘着飘着就沉下来。雨丝落在柳树的叶上,起初是绿得发亮,积得多了,叶尖便垂下来,像噙着泪的眼。晨起推窗,原先是开满花园的各色花,经了这雨,花瓣就蜷了边,连带着墙角的狗尾巴草,也少了几分张扬。
再下几场雨,山就换了衣裳。枫叶先是浅红,被雨一淋,便浓得像化不开的胭脂,沿着山脊铺过去,竟比春时的花海还要热闹。板栗树的叶子黄了,风一吹,便簌簌地落,铺在山路上,踩上去软绵绵的,带着股清甜味。山民们开始忙了,背着竹篓上山摘板栗,收核桃,额头沁出的汗,被风一吹,竟有些凉——先前穿单衣还嫌热,如今薄棉袄也得备上了。
溪涧的水也瘦了,先前哗啦啦地奔,如今却缓了许多,清得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,映着两岸的红黄绿,倒像幅流动的画。傍晚时,炊烟在村子里绕,混着饭菜香飘出来,行人不由自主地紧了紧衣襟,方才察觉风中桂花的香气已悄然淡去,菊花开得正盛——这场雨过后,怕就是霜降了。
柞水的秋,原是藏在雨里的。一场雨,剥去一层热,露出一层凉,把山山水水都洗得分明,也把日子过得扎实。等最后一场雨落尽,雪就该来了,可那又何妨?毕竟这秋,已被记在心里了。(大西沟矿业:卢磊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