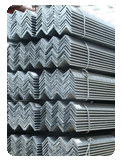老屋偏角静卧着母亲的织布机。那是架带着岁月包浆的木家伙,深色的木纹里藏着阳光的味道,踏板上磨出的光滑弧度,是母亲无数个晨昏踩出的痕迹。它像一位沉默的老者,静静立在时光深处,把岁月织成了绵长的线,又把线纺成了带着体温的光阴。
母亲总爱在暮色漫进窗棂时坐到织布机前,腰杆挺得笔直,她的手指像灵活的蝶,在经线纬线间起落翻飞,木梭子随着她的动作穿梭,在她掌心划出优美的弧线,撞在机身上发出规律的“咔嗒”声,那声音不疾不徐,像大地的脉搏,伴着窗外的鸡鸣和灶间的烟火,和着窗外的虫鸣,成了我最安稳的催眠曲。我常趴在旁边的竹凳上,夕阳从窗棂漏进来,把她额角的碎发染成金纱,看丝线在她膝下渐渐铺展成布,那些单调的白棉线,经她的手一织,仿佛就有了温度。
我总是感觉,当母亲坐在织布机前,便仿佛与机器融合成了一体。母亲眼神专注而温柔,目光凝注在梭子运行的轨道上,仿佛在端详着自家孩子的脸。她动作精准娴熟,梭子来回穿梭,与那哐当哐当的节奏声相合,有节奏地应和着她低低的哼唱,那旋律似有若无,像细雨轻打屋檐,又像春蚕啃食桑叶,在寂静的房间里织出另一层柔韧的声之锦缎,把日子织得绵长而温暖。偶然间,她疲惫地轻叹一口气,声音微细,却透出丝丝的劳倦。她额上沁出细汗,在灯影下幽幽发亮,缠线时弓起的脊背,分明刻着生活重负的痕迹。而我每每倦了,便伏在织机旁边,依偎着刚刚织好的棉布,嗅着布匹间散发出来的草木清香,在机杼声里渐渐沉入安稳的梦乡。
母亲织出的布,是粗厚朴素的土布。这布后来做成了我身上的衣服,穿在身上,虽不甚光鲜,却自有一种贴身的踏实感。布衣洗得多了,颜色便逐渐褪浅,显出些微的苍白来,然而却愈发显出韧性,无论揉搓多少次,也依旧结实如初。那时的我不懂,为什么母亲要花那么多时间在这架老旧的织布机上,直到后来我穿上她做好的衣裳,触摸到布料上细密的纹路,才明白那每一寸布里都藏着她的心意。穿着它,犹如裹着母亲素日里的叮咛与牵挂,虽非轻裘华缎,却足以抵挡窗外风寒。原来布衣之暖,是母亲以岁月织就的茧房。
后来,家里有了缝纫机,再后来,商店里的成衣越来越多,母亲的织布机终于也渐渐停下,后来竟至彻底沉默了。经线纬线早已松弛垂落,如同被时光抽去了力气;机杼不再歌唱,梭子则静静躺在织机一角,沉睡于尘埃中。母亲却总还习惯坐在织布机旁,默默出神,眼光柔和地抚摸着木头的纹理,似乎那经纬之间,仍能浮现出昔日我们围坐嬉闹的身影。
这台织布机便是母亲生命里一架执着打捞时间的器具,母亲以棉线为网,日夜编织,打捞起光阴的碎屑,将它们织成布匹,用以温暖我们一家贫瘠的日子。如今机器虽停,然而那曾经织出的布匹却依旧如新,它们所缝制的一切,皆如一件件朴素而结实的旧衣,裹着我们于人间辗转奔波:纵使行过千山万水,那布纹里针针密密的经纬,早已渗入骨血,成为我们抵御尘世风霜的、最原始也最坚韧的里衬。
如今再回到老屋,织布机依然在角落沉默着,木梭上的丝线早已褪色,可只要轻轻一碰,仿佛还能听见母亲织布时的“咔嗒”声。原来有些温暖从不会被时光带走,就像母亲的爱,永远留在那些被织进布里的岁月里,柔软而绵长。(汉钢公司生产管控中心 徐念龙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