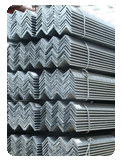立春后,北风卷着雪粒扑向窗棂。我披衣推门,檐角垂下的冰棱正一滴一滴坠着融化的光。倒春寒总在人们卸下防备时悄然回马,像一位严厉的教头,将初出茅庐的春天摁回淬火的铁砧。
巷口的玉兰树最懂这种反复。前日枝头还缀满雪白的花盏,此刻却在寒风中攥紧拳头,把半开的花苞重新裹成褐色的茧。几片倔强的花瓣不肯就范,被风撕扯着掠过青砖墙,落在门环上结出薄霜。我蹲身细看,却见花瓣背面凝结着细密的冰晶,像是春天在暗处绣下的银丝纹样。
城郊的麦田正在经历更为壮烈的修行。嫩绿的麦苗顶着碎雪挺立,每一片叶尖都悬着颗透亮的水珠,折射出无数个微缩的晴空。农人踩着潮湿的田埂走过,靴底翻起的泥土裹着去年的稻茬与今春的草芽,寒热在土壤深处交替更迭,惊醒了蛰伏的蚯蚓。它们扭动着钻出地面,在雪泥间划出暗红的轨迹,像大地刚刚渗出的新鲜血脉。
河边的老柳树最是狡黠。垂丝上冒出的芽苞冻成了翡翠珠子,却在背风处偷偷洇出鹅黄。折下枝条能看见内芯泛青,树汁在冰壳下汩汩流动,如同宣纸上晕开的淡墨。野鸭群掠过河面时,翅膀拍碎的冰凌发出风铃般的脆响,惊醒了浅滩里冬眠的田螺——它们背着螺旋纹路的房子,在春寒中缓慢苏醒。
奶奶往铁炉中添了新炭,说起旧年倒春寒冻死了整片桃林。"可地下的根还活着呢",她掀开陶罐,蒸汽裹着梅子香漫出来,"就像这腌了霜的脆梅,酸里总酿着甜"。窗外的雪渐渐转作冷雨,顺着瓦当滴成珠帘。青石缝里钻出的婆婆纳擎着紫色小花,在雨帘中轻轻摇晃,恍若去年深秋遗落的星辰。
暮色染蓝街道时,风突然转了方向。不知谁家墙头的忍冬藤最先感知暖意,蜷缩的嫩叶舒展开羽毛般的脉络。潮湿的空气中浮动着泥土苏醒的腥甜,混合着远处飘来的炊烟,织成一张无形的网,悄悄打捞起所有冻僵的梦境。
我站在廊下看最后一片雪融进地砖的裂缝,忽然明白倒春寒原是春天最郑重的仪典——唯有经过淬炼的苏醒,才能在往后的风雨里站成永恒的青翠。就像此刻掌中托着的玉兰残瓣,冰霜消融处,裸露出丝绸般柔韧的质地,那是生命反复锻打后留下的真身。